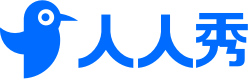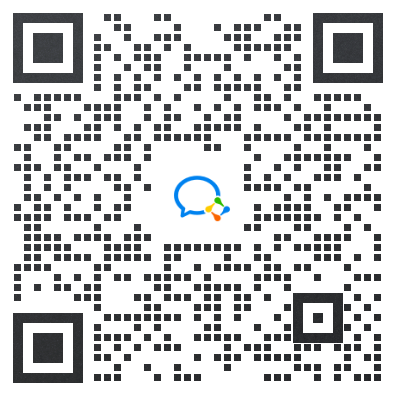至簡(jiǎn)散文
掃一掃分享
發(fā)布者:鵬飛視頻工作室
發(fā)布時(shí)間:2016-04-13
版權(quán)說明:該作品由用戶自己創(chuàng)作,作品中涉及到的內(nèi)容、圖片、音樂、字體版權(quán)由作品發(fā)布者承擔(dān)。
侵權(quán)舉報(bào)